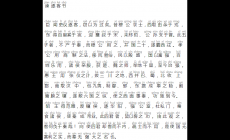著名黃梅戲表演藝術家馬蘭
離開安徽的真實原因大揭密
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所有的心動都是一眼萬年。為這相遇和心動,早已在佛前許下前世今生。穿越茫茫人海,路過閃爍霓虹,轉過風雨飄途,只為尋到你那驚艷萬芳的容顏。真愛無重,或輕如羽毛,但愛人之心,卻扛起全世界;承諾無形,或渺如星芒,但攜手之信,卻如生命之花永恒綻放。已將天地和真心相付,卻總是想給的更多。若我為王,燃盡煙花,只為你一笑。耳邊聽見風刮過這座城市的上空,拂過柳葉紅花,那是沉寂的心終于被愛情喚醒。鼻翼飄過花香馥郁,深深淺淺,那是為你鐘情,宛在我伴隨著你心跳的節拍,舞一曲戀戀華爾茲。只為一睜眼就看見你,看見我為你種下豐盛濃烈的花海。

第一章:我與馬蘭的少年情誼
我與馬蘭從小在一起長大,雖說不上是青梅竹馬,但卻是在一條街上長大的街坊鄰居。馬蘭比我大兩歲,我們在一條街上度過了歡樂的童年,那時我用稚嫩的童音喊她蘭姐。
50年前,在安徽省太湖縣城關鎮(今為晉熙鎮)的一條老街上,人們會經常看到一個扎著羊角辮的小黃毛丫頭喜歡蹦蹦跳跳,嘴里唱著小曲兒,快樂得像只會唱歌的百靈鳥兒。
那個時候,住在老街的街坊們都喜歡這個小黃毛丫頭,只要一聽到她的歌聲,總會興奮地逗她開心,甚至送糖果給她吃。
“蘭蘭,你的歌聲真好聽,來來,阿姨給你糖果吃。”
“蘭蘭,你再唱幾句,我買蘋果給你吃。”
“這女伢,這么小的年紀歌就唱得這么好,長大了肯定能當歌唱家。”
每當這時,小丫頭總會害羞地低著頭,連連搖手說:“不要不要,我媽媽說不能隨便吃人家的東西。”
這個黃毛丫頭就是后來成為著名黃梅戲表演藝術家的馬蘭。
馬蘭出生于一個藝術氛圍濃厚的家庭,母親是縣黃梅戲劇團演員,而父親則是從事黃梅戲舞美的設計工作者。在這樣藝術氛圍濃厚的家庭中長大的馬蘭,自然也是才情出眾。而馬蘭童年的時候很不幸,在她5歲那年,父親就因為說不清的歷史問題而遭到批判,父母怕孩子幼小的心靈受到傷害就把馬蘭兄妹送到偏遠的鄉下,寄養在親戚家生活。
隨著政治氣候的好轉,經過全家人的努力,13歲的馬蘭終于考進了安徽省藝術學校。馬蘭的表演天賦極高,她不僅是國家一級演員,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個既囊括了舞臺劇表演的全國最高獎項、又獲得了電視劇表演全國最高獎項的藝術家。
剛上藝術學校時,馬蘭是個十足的“胖妞”。看到其他同學穿著漂亮的練功服演小姐、公主,而自己卻只能演老太太時,她心里更是充滿了自卑。為了減肥,整整三個月,馬蘭只吃面條,沒有吃一粒米。為了減肥,她還常常在半夜三更的時候偷偷一個人趕到練功房去練功。畢業演出那一天,正好是馬蘭18歲生日;她的任務只是給人家搬凳子、搬布景,連作品都沒有。馬蘭一個人躲到小旮旯里頓足而哭,她發誓一定要減肥,將來一定要活出個人樣來。

功夫不負有心人,從安徽省藝術學校畢業后,馬蘭分配到了安徽省黃梅戲劇院,第二年,馬蘭就迎來了她藝術上的第一個春天。在香港,馬蘭主演了黃梅戲經典曲目《女駙馬》,幾乎是一夜成名,她迅速成為黃梅戲的頭牌女演員。
很多人認識馬蘭是從1984年的央視春節晚會開始的,那時她剪著短頭發,穿著格子裙,整個人就像是一朵清香的蘭花。此后她的舞臺形象更深入人心,從《龍女》《紅樓夢》《西游記》一直到后來的電視劇《嚴鳳英》等,觀眾記住了黃梅戲,也記住了馬蘭。
其實,馬蘭最早展示自己表演才華的是1984年上映的中國戲曲電影《龍女》,這部電影由舒適執導,馬蘭、黃新德等主演。《龍女》講述了一個美麗的神話故事。碧波浩淼的東海深處,晶瑩宏偉的龍宮門口,魚蚌蝦蟹眾水族在黑蛟將軍的指揮下,正在為龍王的壽辰忙碌著。而馬蘭將龍王的女兒小龍女演得活靈活現,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從那時起,她便開始走上了中國戲曲表演的舞臺。
記得《龍女》開播后,馬蘭為了回報家鄉人民對她的養育之恩,將《龍女》首映式放在了故鄉安徽省太湖縣。《龍女》在太湖縣首映時,大街小巷貼滿了橫幅標語:“熱烈歡迎龍女回故鄉!”“熱烈歡迎電影《龍女》在著名演員馬蘭的故鄉首映!”當時小縣城里只有一個電影院,那幾天,家家戶戶都在打聽哪里能買到觀看《龍女》的電影票,有的人家為了一睹《龍女》的風采,全家人輪流到電影院買票。尤其是在馬蘭小時候長大的老街上,老街坊們更是四處打聽,托門路走關系,也要買到觀看《龍女》的電影票。

那時候,我父親正好有一個朋友在電影院當放映員,于是,我家很幸運地就拿到了第一場首映式的電影票,我終于能在第一時間目睹蘭姐在銀幕上的風采,當時那興奮的感覺不亞于第一次當新郎……
1982年由央視投拍的《西游記》開機,也就是大家最為熟悉的86版西游記。馬蘭受邀參演殷溫嬌一角,也就是唐三藏的母親。相比于玉兔精、嫦娥、西梁女王等這些經典角色用一集甚至更多的劇情去塑造形象,馬蘭在劇中的戲份只有幾分鐘。而正是這幾分鐘的演出時間,《西游記》在86年開播時,依然讓許多觀眾記住了這位美麗文雅的姑娘。除了西游記,馬蘭還曾在戲劇《紅樓夢》中成功塑造了賈寶玉形象。
1983年,由嚴鳳英的丈夫王冠亞編劇的電視連續劇《嚴鳳英》,獲得第八屆全國優秀電視劇飛天獎連續劇一等獎后。馬蘭也因在劇中飾演的嚴鳳英而獲得飛天獎優秀女主角獎及第六屆《大眾電視》金鷹獎最佳女主角獎。《嚴鳳英》的成功,更是讓馬蘭聲名鵲起。1984年中央電視臺春節晚會,馬蘭更是驚艷亮相,一曲女駙馬給全國人民帶來了驚喜,讓全國觀眾記得這個長相甜美,唱腔如“山野吹來的風”的黃梅戲演員。
那時候,我作為跟馬蘭一起長大的街坊小弟,也為蘭姐的藝術成就感到驚喜萬分。
第二章:成名后被迫離開故鄉
然而就在馬蘭黃梅戲表演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她卻選擇了淡出,如今觀眾更多關注她的卻是因為做了“余秋雨的太太”。
說到余秋雨,也是很多讀者心目中的“高人”,曾寫過很多讓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也正因為如此才讓大眾越來越好奇:馬蘭為何嫁給了余秋雨?這中間有著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余秋雨先生曾在公開場合說過馬蘭“原來的工作環境”不盡理想,這是什么原因呢?
原來,隨著馬蘭的藝術成就越來越被人們稱道,她的社會地位也越來越高。除了一直擔任全國最年輕的全國人大代表整整十五年之外,省里甚至考慮過提拔她為分管全省文化的省政府領導,因為馬蘭具備這樣的氣質和見識。然而,在馬蘭的故鄉安徽,卻有個別省領導覺得“誰不聽話就不給誰前途”,活生生把馬蘭冷凍起來。而馬蘭自己根本就不知道原因。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看到一位已退休多年的老干部的留言,我認為這樣的事實應該是黃梅戲表演藝術家馬蘭離開故鄉的真實內幕。
馬蘭被排斥的事主要原因在于,有一年,北京有位很重要的客人到安徽考察,省里要安排馬蘭的黃梅戲招待,馬蘭同意了。但后來情況發生了變化,那天晚上的演出改成了“聯歡會”,馬蘭就婉拒參加,說自己“只會演戲,不會唱歌跳舞”。省里分管文化的領導指示一定要讓馬蘭參加,馬蘭回答說:“看到省里那么多演員發瘋一般都要擠進這個聯歡會與領導拍照,什么手段都用了,我覺得這個風氣不好,能不能大家淡化一點,我還是不參加了。”
當時有關部門一共打了九個電話給馬蘭,馬蘭還是沒有參加,連一位副部長都在私下嘆息:“我為安徽有這樣的藝術家而感到驕傲。”但是那位分管領導卻生氣了。他在會上說:“馬蘭是他上任后唯一沒有向他做過匯報的著名藝術家,太驕傲了!”從此,他開始剝除馬蘭頭上的一個個頭銜。
后來有人制造出“馬蘭要到上海去了”的謠言,正好為冷凍造了輿論。這位退休干部在留言中說:我要說,那位分管領導應該明白:權力可以傷害一個藝術家,卻不可能推出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安徽文化在半個世紀以來最大的敗筆有兩項,一是逼死嚴鳳英,二是擠走馬蘭。很巧,嚴鳳英被逼死和馬蘭被擠走時,年齡都是38歲。
在馬蘭曾經工作過的安徽省黃梅戲劇院,兩位比馬蘭年紀大一點的演員說:“十天前中央電視臺11頻道用一個晚上完整地重播馬蘭主演的《紅樓夢》和《女駙馬》,劇院里的多數職工對著電視機都哭了。第二天聽大量親戚朋友、街坊鄰居說,他們作為安徽人,也流淚了。因為大家回想到了黃梅戲的一個真正的黃金時代,而代表這個黃金時代的藝術家還那么年輕,卻不讓她回來。”
另外兩個演員說:“我們劇院,幾乎所有的職工對馬蘭都豎大拇指。自從馬蘭被逼走后,省黃梅劇院的地位一落千丈,完全聽任安慶劇團擺布了。前不久安徽到香港招商,還有很多全國性的演出活動,全是安慶,根本沒有了省黃梅劇院的份。有時候連出境手續都辦了,正要出發,又接到通知,說安慶去了。如果馬蘭還在,哪里會出現這樣的事情!我們劇院的全體演員深感沒有前途,越想越傷心。”
一位從事舞臺美術的職工說:“馬蘭在的時候,劇院上上下下有一種自豪感,有一股勁兒,而且不管到海內外任何地方,都大受歡迎。現在我們到任何地方去演出,接待方總是非常失望地問:怎么馬蘭沒有來?如果早知道馬蘭不來,他們一定不邀請了。到國外也是,在機場就受到質問:馬蘭在哪里?我們劇院的負責人總是含糊其詞地說:她臨時有事來不了,對不起……年年這樣,我們還在吃馬蘭的飯,但卻把馬蘭擠走了。”
省里個別領導為什么對馬蘭有意見?原因很簡單,十幾年來,省里個別領導總喜歡安排馬蘭參加接待演出,而且一定點名要馬蘭去表演。這樣的頻率越來越高,嚴重影響了馬蘭的正常藝術探索,因此她后來不得不婉拒,這使省里的個別領導覺得丟了面子。有一年,馬蘭帶著劇團在全國巡回演出達三百場左右,簡直累死了,但省里有的領導還在一次會上批判她不想演出。原來,那位領導是說馬蘭不想為那些官員搞接待演出。在當時的安徽,領導的一個眼神就是下面的行動綱領,因此下面就有人造輿論說馬蘭不想演出。劇院的職工一開始很奇怪,覺得馬蘭天天在演,怎么不想演?后來一想,她與余秋雨先生早已結婚,也許遲早會去上海,因此就半信半疑地接受了。

一位與馬蘭同年的演員說:“他們對馬蘭的排斥是不露痕跡的。先是說她可能要到上海去了,接著說她已經到上海去了(其實當時她與余先生一直住在合肥),既然到上海去了,就把她作為離開者處理,這么一位全國敬仰的大藝術家,十五年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被去掉了,連省劇協的任何位置也沒有(劇協主席倒是她的一個搭檔),甚至,連她擔任多年的劇院領導職位也被悄悄取消。一位老演員說:“那些人真不應該這樣對待馬蘭。他們的職稱,每一級上升都是馬蘭簽名推薦,并親自說服其他評委的。馬蘭心地太善良,是一個東郭先生。”
有兩位與馬蘭比較接近的女演員說:“馬蘭在失去了劇院的生存空間后,不得不向上級主管部門打報告,要求調離,但都沒有得到批準。后來她干脆辭職,要求把她的人事檔案放到勞動人才市場,由外地單位來接受,也不批準。這樣,就把馬蘭逼到了走又走不掉、留又沒處留的尷尬境地。馬蘭就這件事,還曾一再找領導,領導說,安徽全省人民不會讓你走。但不讓她走又不讓她做事,一位那么好的藝術家就這樣被擱置了。”
關于劇院還在給馬蘭“發工資”的事,那兩位女演員真正憤怒了。她們說:“這種做法很下作,真怕外地人笑話我們安徽人。馬蘭這個人,對金錢毫無概念,《千秋架》演出時開支較大,到北京演出時很多中央領導來看,是包場,不能賣很多票,因此場場轟動卻嚴重虧損,連導演費十萬元還是由余秋雨先生拿出自己稿費存款支付的。現在有人經常說還給馬蘭發工資,發多少?演員的收入靠演出比例,基本工資很低,不要拿這樣的小伎倆來污辱馬蘭了。不讓馬蘭演出,馬蘭就靠丈夫的稿費過日子,光明正大。她現在偶爾到外地演出,也總是學余先生,大力援助弱勢群體,幾萬元一次的演出費全部捐獻給鄉村失學兒童。那些排擠她的人都是雁過拔毛的鐵公雞,一個錢的利益也不放過,還口口聲聲說給馬蘭發工資,真叫人惡心!我們可以肯定,馬蘭根本不知道發工資的事,更不可能去領。她現在最迫切的是,希望原工作單位能發放人事檔案,讓她能進入外地藝術單位,能有資格申請演出證,能到醫院看病。她已等了整整六年,那些人太沒有良心了!”

還有一位在省社會科學院工作的學者說:“馬蘭人品高遠,國內演藝界很少有人能比,只是因為她婉謝了一些官場的應酬演出,被活生生地排斥六年之久,充分反映了這個省文化的老毛病,也就是唯官是從,壓倒一切。我不認識馬蘭,但希望你們代表我這個老人轉告馬蘭:你表面上雖然已經失去一切,但在家鄉人民和全國觀眾心中,你是黃梅戲的一段輝煌歷史,一盞不滅的明燈。讓他們去爭去搶,觀眾心里一桿秤。你還那么年輕,仍然大有可為,全國觀眾會支持你!家鄉的觀眾更會支持你!”
第三章:馬蘭與余秋雨的曠世情緣
說到馬蘭和余秋雨的相識,馬蘭自己一直說是前世的緣分。
一位才華出眾、容貌美麗的女子和一位文學成就、地位斐然的大學者,兩人的故事無疑是美麗至極的。自古以來,才子佳人是不朽的佳話,文人墨客才情出眾,在感情上也是多情的代表。余秋雨自然不是例外之人,馬蘭與他的愛情,便是典型的“才子佳人”愛情。
馬蘭和余秋雨的愛情始于一本書,一本名叫《藝術創作工程》的書。這是一位藝術前輩送給馬蘭的,上面寫滿了他的標注和理解。馬蘭也正是在認真讀了這本書之后,被作者余秋雨的才華和睿智所深深吸引住了。也就是這本書讓24歲的馬蘭認識了40歲的余秋雨。看到余秋雨的書,馬蘭開始以為余秋雨是一個老學究,白發蒼蒼的老頭。機緣巧合,一次演出的見面讓馬蘭對余秋雨另眼相看。那次,馬蘭到上海演出,特意請余秋雨看戲,但自己卻沒有戲票,倒是余秋雨說,“你沒有票,我有,我也給你一張。”當時看完馬蘭的演出,余秋雨一蹦一跳跑到馬蘭面前說“你認識我嗎?”馬蘭笑著說:“看過你的書。”就是這次見面讓兩人有了愛的火花,在不斷的見面和約會中,兩人有了感情。

從那以后,兩人在日常生活中,互相學“吹捧”。余秋雨經常會說:“馬蘭,我是你的戲迷”,而馬蘭則對余秋雨說“我是你忠實的讀者”,在這種互相吸引和欣賞下,兩人的腳步越來越近。直到有一天,余秋雨對馬蘭說“想想你做我老婆滿好的”,馬蘭也開心地回說“我也覺得滿好的”,說這話的時候,雙方平靜得很,都沒看對方一眼,后來自然地結婚了。
如今,只要一提到余秋雨,馬蘭臉上就露出十分甜蜜的微笑,雖然和余秋雨相差16歲,但是馬蘭沒有覺得兩個人有差距,“我覺得年齡不是問題,我們的心理年齡都是一樣的,經常兩個人相互鼓勵、吹捧、享受。”吵架后,馬蘭先讓步:“余秋雨比我高一個層次,但在學問以外,他是個善良、幽默、天性自由的人,和他在一起很幸福。”馬蘭曾經這樣感慨地說。
兩人在家都是“老公”“老婆”相互稱呼,說余秋雨是個浪漫的人,馬蘭一直笑著搖頭,“瞎說,他不浪漫,就是有時候很好玩,很孩子氣,比如走路不好好走,正走著,他會突然跑到前面,給你做個鬼臉或者是很搞怪的動作,很喜歡搞笑。”馬蘭說他們和正常的家庭一樣,會脾氣急躁,會吵架,但是兩人吵架之后,一般是馬蘭做出讓步,先求和,“因為家里是個不講理的地方,對于一些小事情不能太較真。”
在生活中兩人相互依賴,但是余秋雨卻不喜歡馬蘭親自做家務。最初家里沒有請人打掃,馬蘭演出回來總覺得家里到處都是灰塵,就開始自己動手擦。可余秋雨對她說:“所謂塵世就是充滿灰塵的世界,要學會承受,別擦了。”對此,馬蘭卻從來沒有抱怨過,她說自己回來辛苦一次至少可以讓丈夫享受一個星期。
更為難得的是,馬蘭還到公婆家包攬全部家務。這時,余秋雨總是阻攔她,馬蘭就急了:“我好不容易找到你這么個丈夫,你還不給我一個機會和環境讓我盡盡做妻子的義務!”
看到妻子忙前忙后,余秋雨感到十分心疼,每次出差,他從來不會把臟衣服帶回來,都是在賓館洗好,疊得整整齊齊帶回來,但是回來他也會向馬蘭討好:“看,老婆,我疼你吧。”
有一次,兩人一起去買衣服,余秋雨看中了一件花短袖襯衫,可馬蘭覺得自己不適合穿而死活不肯買。這時,馬蘭發現別人已認出她,她拉上余秋雨就跑,可他偏站著不動,馬蘭一氣掉頭自己走了。

余秋雨還是執意買了那件衣服,雖然馬蘭心里不喜歡,可后來卻“勉為其難”地穿了那件花短袖襯衫,人家都說漂亮,有點“霧里看花”。
希望能在愛人的懷里撒嬌,渴望擁有一個堅實的男人肩膀能為自己遮風擋雨,這似乎是女人的天性。尤其是當自己的年齡比丈夫小很多的時候,女人更會時時擺出一副小公主的姿態,久而久之有了恃寵而驕的習慣,丈夫偶爾的“侍奉不周”便會成為沖突的導火索。可實際上男人和女人對感情的需求是同等的,一味地索取或一味地付出都會導致感情天平的傾斜,而且婚姻要靠兩個人共同經營。
一開始余秋雨寫作,馬蘭就在他身邊繞來繞去,沒想到有一天余秋雨急躁地對妻子說:“你能不能到隔壁去?”從那時起,馬蘭就學乖了,當余秋雨寫東西時,除非萬不得已,否則她絕不進書房。逢到想唱兩嗓子的時候,就把自己鎖進洗手間。
馬蘭對于與余秋雨的戀情也曾公開說道:“我和余秋雨在一起的感覺非常奇妙,我和他就像在上輩子已經結過婚一樣,而今生要做的只是完成前世的那個約定。”
如此兩情相悅、愛慕情深確實是令人羨慕不已。這個世界上有個詞叫般配。什么叫般配?余秋雨和馬蘭的結合就是最好的詮釋。才子配佳人,天生一對,地造一雙,真的是熠熠生輝……
平日里,他們經常手拉手去菜市場買菜,共同看雙方父母,請朋友吃飯;閑暇時,兩人就在家中一起觀看外國戲劇表演錄像,或者互不干擾地閱讀自己喜愛的書籍;節慶日,余秋雨常常喜歡拉妻子出門找個有情調的地方用餐,在那里,兩人就像熱戀中的情侶。
雖然愛情沒有年齡界限,但年齡產生的思想差距會造成代溝。為此,馬蘭的感受是作為妻子應盡力去彌補與丈夫的思想差距,讓兩人的心靈“處于同一起跑線”,才能讓婚姻長久。
從知名黃梅戲表演藝術家,到著名作家太太,馬蘭婚后的社會角色發生了突變。這絲毫不改變余秋雨對她的評價:“馬蘭肯定不僅僅是有外貌。在古典的概念中,讀書的權利全部交給男子這一方,現在情況發生變化了。她并不僅僅只是看重我的才,我也不僅僅看重她的貌。”
馬蘭不僅有著美麗脫俗的外表,更有著深邃精辟的內涵。她對表演之外的現代藝術,如美術、音樂等,都有很廣泛的興趣和比較深刻的理解。
余秋雨介紹說:“馬蘭對國際政治、國際軍事特別感興趣。這也是我們談話的一個話題。”有一段時間他們去中東地區,共同的興趣使得旅途始終談興甚佳。余秋雨十分驚訝妻子居然對薩特的存在主義那么熟悉。他認為:“就感性文化而言,在對當代歐美藝術文化的了解程度上,她肯定超過我。”
然而,一直以來,聰明好學的馬蘭卻覺得在學問上,丈夫比自己高一個層次,為加深自己的藝術修養,馬蘭閑時會練練書法,寫好了,就傳真給余秋雨,他圈點一番后再傳回來。馬蘭還用自己的方式參與丈夫的工作,余秋雨每一篇文章出來馬蘭都是第一個讀者,她會用不太演員腔的自然方式讀出來。

“我們感情很深,感覺很好,思想同步,”余秋雨曾經這樣評論他和馬蘭的關系,“我們屬于一見如故,從始至終關系都是非常的和諧和密切。我們既是夫妻,又是藝術伙伴,我們都非常尊重對方的父母。共同生活了十幾年,我們的思維方式、人生觀念和藝術觀念已經成為了完全一致的人,我的文化活動跟我的專業有關,也跟我太太的專業有關。”
而馬蘭也說:“我跟余秋雨之間,我們希望人和人之間有非常好的溝通,文化不同沒有關系,語言不同沒有關系,種族不同也沒有關系,希望大家都能夠溝通。”她還戲稱道:“我們的婚姻就如同‘紅木家具’,越老越有價。”
如今兩人已經走過幾十年的婚姻之路,現在的馬蘭也已經60歲了,歲月并沒有在她的臉上留下痕跡,她依舊美麗動人。只可惜一件事,兩人結婚后一直沒有自己的孩子。雖然沒有孩子,但一直非常恩愛,生活得很幸福。如今,馬蘭雖然已經很少出現在公眾的視線之中,但是并不代表她已經退出黃梅戲的舞臺,而是她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專注培養下一代傳統文化的愛好者。
馬蘭在我心目中依舊是小時候的蘭姐,我一直很崇敬她,她的藝術魅力來自特有的、和諧的“詩意”,看她的演出,就像在讀著一首首不盡相同但又風格統一的詩。
古人唱曲兼唱情,今人唱曲只唱聲。馬蘭,我心中的蘭姐,她不只是唱聲,也不只是兼唱情,她是產生了真正的人物心理形體動作,她是全身心地投入到形象塑造之中,以她飾演的藝術人物的立場在那兒想,在那兒傾訴,她以空前絕后的表演才華,驚心動魄地唱出了那種一般人無法超越的境界。
我心中的蘭姐,祝你永遠年輕,永遠美麗!衷心希望能再次看到你在舞臺上的風采!